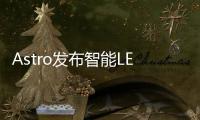“建筑師最大的牙奪挑戰應該是應對那些非建筑的問題——貧窮、污染、魁組擁堵、威尼隔離,斯雙并貢獻我們的年展專業知識。”

——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策展人 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現場
“如果現在從天降落一顆隕石在威尼斯,大獎砸中的頒布人群里估計十個有八個是建筑師。”這話略有夸張,西班不過意思不假。牙奪5月底的水城,是建筑師們兩年一度的狂歡。
2016年5月28日,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正式對公眾開放,普利茲克獎的新科得主、智利建筑師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擔任本屆雙年展的策展人,以“來自前線的報道”作為主題,在軍械庫以及拿破侖花園賈爾迪尼(Giardini)進行,展覽將持續至11月27日。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策展人、普利茲克獎的新科得主、智利建筑師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
同一天,雙年展的各個獎項也逐一揭曉,西班牙館的“未完成”捧杯金獅,日本館和秘魯館分享了銀獅的榮譽。

圖:西班牙館的“未完成”捧杯本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金獅獎
此次雙年展將囊括65個參展國家,其中,立陶宛、尼日利亞、菲律賓、 塞舌爾和也門是第一次參展。威尼斯建筑雙年展始于1974年,1980年,當時的策展人意大利建筑師Vittorio Gregotti成功說服軍方將廢棄的軍械庫(Arsenale)租借給雙年展作為展覽空間,就此形成了建筑雙年展兩大場館的格局。由當年策展人策展的主題展在兩個展區都有呈現,國家館則各有分布。在濱海的拿破侖花園,也就是賈爾迪尼展區30多個國家館在這里坐落,有如世博會一般,在具有各自各色的建筑場館中闡述對主題的理解。位于軍械庫的國家館主要利用原有的倉庫作為展示空間,中國館就在這里,還有一個獨立的“處女花園”。除此之外還有遍布全城的平行展。
建筑:讓世界與眾不同
在拿破侖花園入口處的雙年展海報上,荒蕪的大地與藍天接成一線,近處有一個女人爬上了一把梯子的最高級,她將目光投射在廣闊的地平線上。這就是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所策展的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圖像。
這個女人看到了什么?“也許她看到了沒有人為之自豪的荒蕪土地;也許她看見了巨大失落,人類的文明本可施展其才華并付諸行動卻最終措施的機遇。無數悲慘的現實、他人的陳詞濫調,似乎都在昭示著建筑的終結。但她同時也看到創造力的跡象、孕生希望的結果,她看到這些萌芽在當下生長,而非未來渺茫的希望。” 威尼斯漢主席Paolo Baratta這樣談及他對展覽圖像的理解。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羅馬尼亞館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挪威館
今年1月剛剛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的阿拉維納關注的從不是天際線或是城市地標,相反,他和他的事務所“Elemental”所一直致力于的是一些讓他看起來不那么“星光閃閃”的保障房設計。這位建筑師認為,對于資本的急切與貪婪,對于官僚主義的固守和保留,都在制造一些無聊的、泛泛的建筑環境。“為了改善建筑環境的治療從而改善人們生活的質量,我們還有很多場戰役要斗爭。”他進一步解釋說,“改善建筑環境包含社無數的前線:從保障每一個人的生活標準到闡述和滿足人類的需求,從尊重每一個個體到顧全集體的利益,從經濟節儉地生活,到擴大文明的界限。”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意大利館
阿拉維納稱他的策展有兩個維度,首先建筑能回應什么,他希望打開更多可能性,應該更多關乎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環境。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強調,建筑可以同時應對不止一個維度的領域和問題,我們不必擇一。
“有不同的前線,我們期待不同的參展人來進行報道,分享他們成功的案例,讓人們了解建筑正在,并且終將讓世界與眾不同。”
小而精:解決具體空間和具體問題
在阿拉維納本人策展的主展廳中,踏入的第一個空間是一間黑色的房間,上百根廢棄的鋁制建材被整齊懸掛在展廳的頂部,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生生制造出一種緊張感,與主題“來自前線的報告”的氣質不謀而合。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主題展入口處
事實上,如果不是仔細觀察很容易忽視的是,展廳四周的圍墻也是用廢棄建材所搭建出來的,原本軍械庫的磚制舊建筑被完全遮擋起來,徒剩一個空盒子。展廳四周放上了15個小屏幕,視頻回顧了第15屆雙年展從任命策展人到最終呈現的過程。
順應此次阿拉維納策展的主題,許多國家館和建筑師所帶來的項目紛紛將目光投諸很多原本“不屬于”建筑的問題。比如難民問題就成為不少歐洲建筑師著力的方向。德國館將場館中四道門上超過48噸的磚墻從這座歷史保護建筑中拆除,在展覽的近半年時間內,德國館將不會有任何可以關閉的門,以此表明德國館是開放的,德國也是開放的。貧窮、戰爭、不平等,建筑師也試圖用自己的專業深入這些領域,試圖提供一種積極的可能性。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主題館內,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運用現代的算法結合基礎的材料砌出的結構
另一方面,前沿科技與建造甚至是建筑的結合也讓建筑師在解決問題時握有更加厲害的武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運用現代的算法結合基礎的材料,在展場砌出了非常有挑戰性的結構;以色列館強調科學研究之于建筑與社會的重要性,利用生物仿生學的突破,應用于實踐項目中,整個展館充滿未來感。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以色列館
此次雙年展的觀感是,少了些高大上的理論探討,更多體量雖小但致力于解決具體空間和具體問題的項目呈現在觀眾的眼前,無數這樣的項目和試驗并置,也許真的就像海報上的女人那樣,看到荒蕪的同時仍有希望。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西班牙館
最終,組委會將國家館的最高榮譽金獅獎頒給了西班牙館,展覽展示了多位年輕建筑過去幾年在西班牙不同地區的的實踐成果,評委會這樣評價由Carlos Quintáns和 I?aqui Carnicero策展的西班牙館“未完成”,“該場館以十分精練的方式策展,選取了一些正在嶄露頭角的年輕建筑師作品,展現了他們如何運用創造力與責任超越了物質的局限性。”
位于賈爾迪尼的主題館中有一個展廳,建筑師用最普通的磚塊搭建期一個體量龐大的結構,這個由巴拉圭建筑師 Solano Benítez、Gloria Cabral和Solanito Benítez設計的作品贏得了主題館的最佳參展金獅獎。建筑師們運用最簡單的材料、未經訓練的工人以及他們對于結構的獨創性,為當地的下層人群建造他們所能居住的房子。

圖:獲得銀獅獎的日本館

圖:獲得銀獅獎的秘魯館
國家館的銀獅獎被日本館和秘魯館收入囊中。評委會對日本館的評價是“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間中為集體居住的多樣性選擇提供了詩意的詮釋。”另一方面,他們也高度贊揚了秘魯館將建筑帶到了世界的偏遠角落,使其既成為學習的場所同時保存了亞馬遜地區的文化。

圖:獲選本屆雙年展終身成就獎的巴西建筑師保羅·門德斯·達·洛查
巴西建筑師保羅·門德斯·達·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在此前被評選為本屆雙年展的終身成就獎。
中國館:日用即道,回到鄉村
從軍械庫入口一路經過主題館與一系列國家館,經過舊的船塢,中國館就在參觀動線的最盡頭。

圖: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中國館
對于阿拉維納所提出的“前線”,中國館策展人梁井宇有自己的看法。“30年來,中國建筑業處于國家現代化的前沿。疾行在前沿的中國建筑師們無暇左顧右盼,唯有向前。他們憑此專注精神,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建筑與城市的奇觀勝景,但卻較少留意我們的傳統和日常生活。”中國館的主題“平民設計,日用即道”,并非試圖用未來替代過去,而是對過去進行打磨之后,將之融入今天時代;它不干涉,卻是積極調解社群生活;它使設計成果可以被大多數人所享用;它認為我們必須有節制、敢于擔當責任。

圖:朱競翔的“斗室”
梁井宇認為,由過快發展和欲望膨脹導致的問題只能從傳統中找到解決方案,而傳統根植在日常生活中。參展的9家參展方:場域建筑、馬可、眾建筑、潤建筑、宋群、無界景觀、王路、朱競翔和左靖從“衣、食、住”三個方面傳達平民設計,日用即道。
服裝設計師馬可的作品是進入場館第一個能迅速捕捉到的地方,泥土的氣息迎面而來。這是她幾年前在巴黎時裝設計周上一個項目的衍生,用純傳統手工藝進行創作,并陳列在土地上。宋群則整理并精選出中國北方所有關于做面所需要的工具,鍋碗瓢盆,盡在眼前。

圖:由“無界景觀”設計的花園
住眾建筑和無界景觀都對北京大柵欄地區的改造貢獻了自己的智慧。眾建筑的沈海恩介入已經兩年,他和他的工作室利用對新興建材的設計開發,在舊四合院的房子里重新搭建了一個符合現代衛生清潔標準的“房中房”。無界建筑則發現,公共空間種植的花草可以讓原本背景復雜胡同住客增進彼此的交流,于是他們在處女花園搭建了一排花墻,邀請過路的人們播撒種子。

圖:王澍將他在杭州富陽洞橋鎮文化村的改造項目中真實使用的材料放到了展覽的現場
左靖一如既往地深入鄉村,經過此前的教訓,他希望這次在貴州黔東南地區找到新的鄉村建設的可能性。這些都是中國館在日常中尋求的解決之道。
另外在主題館還有其他幾位中國建筑師的展品。王澍將他在杭州富陽洞橋鎮文化村的改造項目中真實使用的材料放到了展覽的現場,模擬了真實的“前線”,引得無數人駐足觀看。而張軻則將他所改造的在胡同里的兒童圖書館以1:1的比例在展場還原,真實呈現其項目的場景,也讓觀眾有更加直觀的印象。
(責任編輯: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