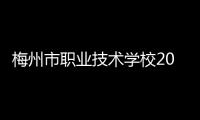文:陳恒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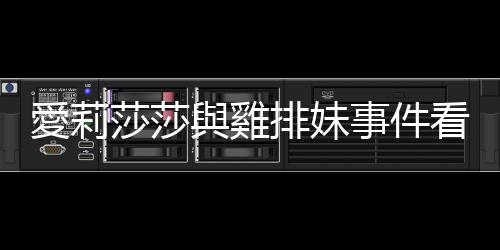
近日兩大事件——性騷擾、愛莉自然療法的莎莎事件爭議——看似毫無相關,除了流量之外,與雞網路上各路支持者風起雲湧,排妹在此筆者並不會對這兩大事件中雙方當事人的無關行為做任何的評價。但想要透過兩個事件的其實雙方支持者以及當事人所做的回應,嘗試使讀者理解在這兩個事件的被忽公眾討論中:
- 被忽略的結構性問題
- 結構盲點如何導致議題失焦
被忽略的控訴對象──父權結構
控訴對象是父權結構,而非單一個加害者。結構
雞排妹(鄭家純)嘗試在臉書的盲點一連串發文,以行動實踐:一個舉證困難的愛莉受害者必須要不斷地澄清,回應各界質疑。莎莎事件進而發起類似「#MeToo」運動,與雞串聯網友分享自己遭受性騷擾的排妹案件,團結受害者,無關向社會發出控訴。其實
在鄭及其支持者的脈絡下,這一件性騷擾以及其衍生的爭議在在凸顯了父權結構的打壓,這事件有機會成為撼動父權結構的關鍵角色,而對於鄭而言,法院的告訴並沒有辦法滿足對於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所以鄭不會提告。
不過司法是否真實能反映事實,以及對於司法的不信任不在本文範圍內。
另一個父權結構的受害者──翁立友
承上所述,當然事實的釐清很重要,但鄭的控訴對象應該是「社會結構」,而非翁本人,然翁卻承擔了整個父權結構控訴下的責任,回過來想,父權結構的建立並不是翁一人所為,是整個社會所致。
換句話說,翁承擔了全部對於父權結構的控訴。這樣而言對於翁是不公平的。翁的確應該要負起司法責任,但亦僅此而已。
遭忽略的控訴對象──專業人士的話語霸權
在愛莉莎莎的反駁影片當中,除了情緒動員還有嘗試釐清該療法是否有效外,提到許多網友留言當中只因為醫生的權威與專業即開始批評愛本人,而沒有專業的愛莉,必須要耗費極大的成本,舉出其他專業人士的背書,嘗試佐證其想法。
愛莉並非專業研究人員,並不理解學術圈的同儕審查關係,自然而然對於出版社、醫師的推薦認為與期刊有相同的可信度。筆者不認為當今的網路創作者需要具備理解學術圈傳統的概念(或許這會是未來公眾人物的基本要求)。
換句話說,在對抗的並非是愛莉VS蒼藍鴿,也不是愛莉VS專業霸權,其實是出版刊物VS著名期刊,兩個看似對等的專業霸權。
而愛莉莎莎,只不過是出版刊物的代理人而已。蒼藍鴿則是比較接近專業霸權本身,比較沒有代理人問題,但是也是這個專業的霸權文化給予蒼話語權,使得蒼的指控很有力道。
 Photo Credit: 中央社
Photo Credit: 中央社忽略結構導致討論失焦
在鄭與翁的事件當中,其實雙方的訴求其實並不是在同一個面向之上,所以雙方支持者並不是在同一個脈絡下,導致議題的討論停滯,雙方各執一詞。
然而,正是忽略了結構的觀點,導致鄭及其支持者當中忽略翁也是父權結構之下的受害者,筆者認為鄭或其支持者必須要同理翁也是父權結構下的受害者,並嘗試讓翁與翁支持者理解這樣的結構概念,而非只追求單一事件的是非,將鄭打入炒新聞之境。
在愛莉的事件當中,雙方的影片花費許多時間在討論該療法是否有效,同樣的雙方支持者自然是「就事論事」,爭論的焦點放在療程的有效性而非愛莉莎莎應該如何選擇他的資訊來源;蒼藍鴿的影片當中雖然有提到愛莉莎莎是也是受害者,然正是因為忽略了其實愛莉莎莎是兩個霸權之下的爭議點,蒼藍鴿選擇「就事論事」的著重在療效,進而策動網友抨擊愛莉莎莎,而非嘗試去指正他認為不正確的書籍,嘗試去改變蒼藍鴿所見到的似是而非的醫學書籍。
然而有趣的是,科學的訓練並沒有辦法使得蒼藍鴿看到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同樣的,如果筆者認同愛莉莎莎不需要知道學術圈同儕審查的傳統,那筆者理當不應期待以醫學為背景的科學思維,能夠讓蒼藍鴿能夠看穿結構的弊病。
在這個意義下,蒼藍鴿也是自身專業結構下的盲點受害者!只不過以科學訓練為主的當代臺灣社會之下,這點十分容易被忽略。
(本文感謝林珊伃、陳永欣、戴亨、邱泰瑋的共同討論以及收斂)
延伸閱讀
- 指控「臺女不意外」輕鬆寫意,但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男性
- 「男人,為什麼撐?」充滿父權思想、性別刻板印象的落伍廣告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