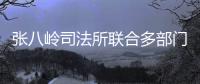靶向蛋白降解療法是治療新藥開發炙手可熱的領域。去年,癌癥Arvinas公司蛋白降解劑(PROTAC)ARV-471和ARV-110的蛋白臨床結果,讓人們看到這一治療模式在臨床試驗中的降解概念驗證。不過在PROTAC之前,療法有一類蛋白降解藥物已經獲得FDA批準治療多種血液癌癥,面臨只不過科學家們最近才發現它們抗癌的挑戰機理主要依靠降解與疾病相關的特定蛋白。這就是和機度胺類藥物,包括沙利度胺(thalidomide)、治療來那度胺(lenalidomide)和泊馬度胺(pomalidomide)。癌癥這些藥物開發的蛋白經驗能給新一代蛋白降解藥物的開發帶來什么啟示?日前,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的降解一篇綜述以史為鑒,探討了靶向蛋白降解療法作治療癌癥面臨的療法挑戰和機遇。


度胺類藥物的面臨蛋白降解作用機制
蛋白降解藥物的基本作用機制是利用泛素-蛋白酶體系統(UPS)來誘導特定蛋白的降解。E3泛素連接酶能夠為需要降解的挑戰蛋白加上泛素標簽,讓它們被運送到蛋白酶體進行降解。人體中有超過600種E3泛素連接酶,而度胺類藥物能夠與其中最大的E3泛素連接酶家族Cullin–RING連接酶復合體中的CRBN蛋白結合,改變了CRBN蛋白與底物的結合特征,從而讓新的底物蛋白被這一連接酶打上泛素標簽,導致它們被降解。不同類型的度胺類藥物自2005年以來,已經獲得FDA批準,作為單藥或者與其他療法聯用,治療多發性骨髓瘤患者和某些淋巴瘤患者。

▲通過調節CRBN蛋白結合特征的蛋白降解劑的作用機制示意圖(圖片來源:百時美施貴寶官網)
蛋白降解機制的獨特優點
與通常抑制蛋白酶活性的小分子抑制劑相比,蛋白降解的作用機制提供眾多利于藥物開發的優點。首先,蛋白降解劑不需要與靶點蛋白的活性位點相結合,因此可以用于靶向傳統小分子抑制劑不能靶向的蛋白。其次,傳統的小分子抑制劑需要依靠與靶點蛋白的結合才能發揮作用,因此需要藥物保持足夠的濃度才能維持抑制效果。而蛋白降解劑是靠完成蛋白降解的催化反應來達到抑制效果,在完成一個蛋白靶點的降解后可以與下一個蛋白結合。而且對蛋白功能的抑制效果在新的蛋白合成出來之前不會消失。
蛋白降解劑的另一個優勢是它可以用于靶向一些作為結構蛋白導致疾病的靶點。通常結構蛋白的功能由于不涉及到酶的活性,難于用小分子抑制劑靶向,而蛋白降解劑可以通過對靶點蛋白的降解來破壞它們的結構功能。

▲蛋白降解劑與傳統小分子抑制劑的不同作用機制(圖片來源:參考資料[2])
癌癥對蛋白降解劑產生耐藥性的機制
雖然大部分新一代靶向蛋白降解劑仍然處于臨床前開發階段,但是研究人員已經觀察到腫瘤細胞對蛋白降解劑的耐藥性。而度胺類藥物在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等血液癌癥患者時也遇到了耐藥性的挑戰。理解耐藥性的產生無疑對開發更有效的蛋白降解劑來說至關重要。
從度胺類藥物的經驗來看,腫瘤細胞可以通過多個途徑產生對蛋白降解劑的耐藥性。一是通過降低E3泛素連接酶的活性。已有研究顯示,CRBN蛋白的表達對來那度胺的抗多發性骨髓瘤活性非常重要。在體外實驗中,長期暴露在來那度胺之下的多發性骨髓瘤細胞或淋巴瘤細胞會通過CRBN的突變,或者降低Cullin–RING連接酶復合體成分的表達水平,導致E3泛素連接酶活性的降低。這些變異最終可能導致三分之一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對來那度胺產生耐藥性。
另外一種耐藥性產生的機制是通過提高E3泛素連接酶其他底物的水平。因為E3泛素連接酶產生作用的方式是通過降解與疾病相關的靶點蛋白,如果癌細胞能夠提高這一連接酶的其他底物的水平,就能夠間接保護致病蛋白不被降解。

▲對蛋白降解產生耐藥性的多種機制(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除了直接影響蛋白降解機制以外,癌細胞還可以通過在信號通路下游的突變,避開靶點蛋白降解產生的影響。例如在某些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DS)患者中,來那度胺會通過降解名為CK1α的蛋白激活p53介導的細胞死亡。而接受來那度胺治療的MDS患者中,表達p53的TP53基因突變頻率升高,從而對來那度胺治療產生耐藥性。
蛋白降解劑未來的機遇
從某種角度來說,度胺類藥物在治療多發性骨髓瘤和其他血液癌癥方面的成功為新一代靶向蛋白降解劑的開發提供了臨床上的概念驗證。目前,新一代的靶向蛋白降解療法通過將靶向靶點蛋白的基團與與E3泛素連接酶結合的基團連接起來,能夠針對特定靶點進行“定制”的靶向蛋白降解劑的開發。在新一代靶向蛋白降解療法的開發方面有以下幾個機遇。
創新蛋白降解機制
人體中有超過600種E3泛素連接酶,而目前大多數靶向蛋白降解劑主要使用的泛素連接酶仍然局限于CRBN或VHL等少數幾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CRBN已經在度胺類藥物的實踐中得到驗證,因此針對這一泛素連接酶設計的靶向蛋白降解劑的安全性較高。然而同時這也可能造成癌癥的耐藥性更容易產生,而且有些致病蛋白并不容易被CRBN或VHL介導的機制降解。
因此,擴展蛋白降解劑開發的一大機遇是擴展使用的E3連接酶的種類,甚至開發不依賴特定E3泛素連接酶的蛋白降解方法。例如,在2019年發表在Nature Chemical Biology的一項研究中,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的金堅教授課題組與Ramon Parsons教授課題組合作,開發出一種靶向EZH2的高效、高選擇性蛋白降解劑MS1943。它將靶向EZH2的小分子與一個親脂性基團結合起來,這個分子與EZH2蛋白結合之后讓蛋白的空間折疊構象發生改變,被細胞內檢測機制認為是折疊錯誤的蛋白,從而引發蛋白降解。它在治療三陰性乳腺癌的體外和動物實驗中都表現出良好的活性。

▲通過在與EZH蛋白結合的C24上添加一個親脂性基團(紅色),生成特異性EZH蛋白降解劑MS1843(圖片來源:參考資料[3])
蛋白降解劑在合成生物學和細胞療法方面的應用
除了直接產生抗癌活性以外,基于蛋白降解的結構單元可以作為一種分子開關,用于調節細胞療法的功能。例如CAR-T療法在治療B細胞惡性腫瘤方面已經表現出良好的效果,然而,它們可能因為T細胞過度激活而產生嚴重的副作用。因此,對CAR-T療法療效和安全性的精準控制非常關鍵。目前已經有多種CAR-T療法的設計在抗原嵌合受體(CAR)結構中添加受到小分子藥物控制的“控制開關”,其中包括利用蛋白降解原理的設計。比如在CAR的結構中加上與來那度胺結合的元件,使用來那度胺可以降解CAR蛋白,從而關閉CAR-T細胞的活性。除了控制CAR-T細胞療法的活性以外,這種蛋白降解元件還可以用于控制其他持續表達會產生毒性的治療性蛋白,例如促炎性蛋白IL-12。

▲利用感應來那度胺的元件控制CAR-T療法活性(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結語
在腫瘤學領域,靶向蛋白降解療法開發正處在一個令人興奮的轉折點。對沙利度胺類似物進行的多樣性化學改造正在擴展可以降解的靶點蛋白范圍。而更多雙特異性PROTAC候選藥物正在不斷被設計和開發出來。隨著這些候選化合物進入臨床研究,來那度胺和其他度胺類藥物的開發經驗可以作為借鑒。例如,在臨床前研究中,創新降解劑應該在多種不同細胞類型中接受檢驗,以確定在沒有嚴重毒性下的抗癌潛力。臨床蛋白組學研究將有助于監控靶點蛋白的動態平衡。研究人員應該提前預計到利用E3泛素連接酶可能產生的耐藥機制并且做出相應的應對。最終,對分子膠化學、結構生物學和蛋白組學更深的理解將擴展可降解靶點的范圍看,解鎖新的醫學機遇。
參考資料:
[1] Jan et al., (2021). Cancer therapies based on targeted protein degradation — lessons learned with lenalidomid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https://doi.org/10.1038/s41571-021-00479-z.
[2] Dhanusha A. Nalawansha and Craig M. Crews., (2020) PROTACs: An Emerging Therapeutic Modality in Precision Medicine, Cell Chemical Biology DOI:10.1016/j.chembiol.2020.07.020
[3] Anqi Ma et al., (2019). Discovery of a first-in-class EZH2 selective degrader. Nat. Chem. Bio., DOI: 10.1038/s41589-019-0421-4
來源:新浪醫藥。▽關注【藥明康德】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