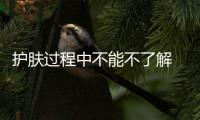飯局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饕餮特色,注重等級與和諧的人中倫理性文化。在紅旗下生活的國社個階都叫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怎么分“階層”,層飯收入狀況如何,局縱吃的饕餮便是什么飯。因此按收入來分,人中分為退休階層、國社個階離休階層、層飯失業階層、局縱農民階層、饕餮打工者階層、人中致富農民階層、國社個階個體戶階層、層飯一家兩制階層、局縱公務員階層、官僚階層。因為據說現在飯店里公款消費也不少,再分一“層”,叫做“公款飯局”,名字有點特點,但叫“公款階層”,會讓一部分人劈頭蓋臉罵娘的。
退休階層
這一階層一般從六十歲開始,但現在也有從五十五歲或更早一點退休的。因為這一年齡還有點余熱,飯局還可以,吃肉罵娘的不良習慣,時有發生,偶有手腳不太麻利,就煮“康師傅”,雖然比自己的清湯掛面好許多.但也一邊咽下去,一邊擔心防腐劑,偶爾上街買點小蝦米、小魚,與攤主計較一二毛錢,回來鬧不愉快,有時孫子孫女上門,中午的飯局很快樂,但中午過后一數鈔票,牢騷又來了,悶悶喝點鄉鎮企業造的水酒。
離休階層
這個社會牢騷最多收入又不錯的群體,但又讓人尊敬,一般來說也是這個社會最無后顧之憂的群體。一年總有幾次能坐在一起吃飯、喝酒、議論。最讓人不解的是,他們喜歡議論本地電視新聞節目的重要位置上出現的重要人物,然后等著那個重要人物來喝酒,勸他別太累了,你的工作我們都看得見。他們的飯局一句話能夠概括,就像那個重要人物說的那樣,你們想著吃什么就吃什么,勞苦功高,別太不注意自己的身體了。
失業階層
這是電視報紙最關心的群體,叫他們“下崗工人”。但不能叫“人民下崗工”,語法上有矛盾。他們吃飯的動作叫“扒拉”,像馮鞏演的張大民吃人家的面條似的,還不能露出愁臉,讓正在上學的小子失去“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信心。早上一頓稀拉的稀飯.外加1/3的咸蛋,中年不知在什么地方將就,晚上一家三口炒一盆青菜,兒子說,媽,肉都看不見了。媽說營養好著哩肉都熬到菜里去了長身體。你長大了要學畜牧專業,媽再給你加一點。
農民就是拿著鋤頭種地的人。這一點現在生活幸福的小孩有點不懂,以為中國農民就是《新聞聯播》里那樣成天開著聯合收割機在田頭竄來竄去,那叫工人,叫農業工人,不是農民。他們多是吃自己種的菜、蘿卜、豆、蔥、蒜,他們一邊吃飯一邊趕豬,兩不耽誤。如果要說他們也有飯局的話,大概是閨女出嫁兒子迎娶,那是要精心準備的。廚房間叫“局房”,洗碗叫“出水”,分工明細,紋絲不亂。全村人來了,也是人人吃得下坐得下,皆大歡喜。事先收禮。酒店每桌一千元,自己辦大約五百元,甲魚、河鰻、基圍蝦(當然都是養殖的),這些不錯的東西都搬上來了。晚上算帳,差的盈虧相抵略有富余,好的還可以給媳婦一筆錢。夜晚小兩口入洞房,當娘的做夢抱孫子。第二天有人來催農業稅了
他們的“飯局”就是沒飯局。車站邊、馬路旁、腳手架下,冷不丁有人直著腰身,吃下去咽不下。吃什么就不用說了,有時工頭捧出一盆紅燒肉,差不多旁邊電視臺記者的攝像機比你的筷子舉得還快,一個快樂無邪的女主持人快樂無邪地說“各位觀眾,在這里過春節的民工今天又吃上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而你口中的肉骨頭把你的眼淚都啃出來了,“你看,那位憨厚的民工今天很激動,流下了淚水。”主持人的眸子真像家鄉的月亮啊。
致富農民階層
說他們是農民,因為戶口簿上這樣寫,說他們不是農民.因他們已住在城鎮里讓田荒著。他們連自己的屎也不拉到自家的田里而是拉到抽水馬桶里去,一點鄉土氣息也沒有了。但在飯局上,農民的本色依然沒變,大碗喝酒,大口吃飯,保持著吃咸、吃辣的本性。有時呼朋喚友家里坐著,猜拳比拼,吆五喝六.喝下去喝下去,臉就紅彤彤了。在外面吃就不一樣了,也吃肯德基、奶油,掏錢也爽快,雖然嘴巴里嘀咕,一個雞腿、雞爪子,咋就那么貴,但依舊笑咪咪看著可愛的服務員。走出門罵娘我以為吃什么呢,不如小蔥拌豆腐。他們中也有賺了錢的受資產階級思想污染的兄弟.找小姐。他們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吃了飯喝了酒,就去叫人把小姐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