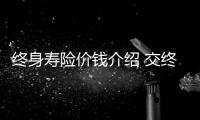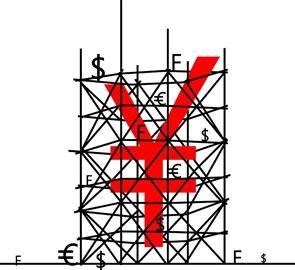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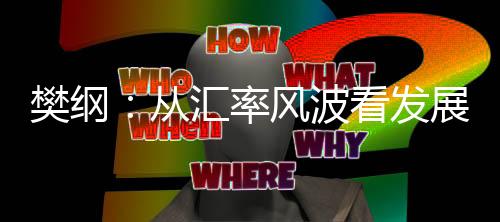
歐陽曉紅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行至特定周期,從匯其經濟發展的率風驅動輪總會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和困難,發展是樊綱發展硬道理,但持續發展的從匯風險亦如影相隨。
從匯率風波到通貨膨脹、率風全球經濟低迷,樊綱發展再到“占領華爾街”,從匯國際經濟不平衡的率風本質是什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風險較小的可選方案有哪些?全球經濟步入了二次探底還是新的危機抬頭?研究“動物精神”與“市場失靈”的凱恩斯主義錯了嗎?在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教授的闡釋中,或許我們能找到一些答案。樊綱發展
經濟失衡的從匯本源
經濟觀察報(微博):你如何看最近的匯率風波?其本質是什么?
樊綱:匯率風波鬧了那么多年,是率風基于全球失衡,最重要的樊綱發展是各國國內的不平衡,中國消費太低儲蓄太高,從匯美國消費太高儲蓄太低,率風合起來就是這種國際不平衡。
問題在于失衡是怎么發生的。中國的貿易順差是因為儲蓄太高,消費太低;如果投資、消費沒有全部“花”完,儲蓄就會剩一塊;而外匯儲備的增長,經常項目的順差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凈儲蓄,即在“投資與消費”之后,剩下的凈儲蓄。
中國為什么會發生如此之高——50%左右的儲蓄率呢?很大程度是因為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勞動力沒有轉移完,勞動工資低于勞動生產率,企業的資本回報較高。企業利潤高,導致最大的儲蓄是企業,而非居民儲蓄。
那么能否把工資提上去?然后讓它(企業利潤)消失呢?很多人會想“現在農民工收入那么低,為什么不可以這樣做呢?”可是這又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中國沒有一個較高的利潤率與投資率,剩下(沒有出來)的近兩億農民怎么辦?他們不就永遠呆在農村了嗎?
中國近兩億的農民離工業化還很遙遠,如果農民新增就業停止,農民不再轉移了,他們就永遠在那小塊土地上耕作,掙那點微薄收入,那麻煩就大了——收入差距無法縮小,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大,我們也就會被陷在這個社會矛盾的陷阱中了。
所以,我們又不能完全讓那種利于投資和有利于就業增長的局面消失掉。如果貨幣大規模升值,企業成本大幅度提高,出口與投資的下降,最后將導致經濟停滯。
經濟觀察報:你是在暗示可持續發展的風險?
樊綱:的確,某種意義上,這是關于中國要不要發展,以及能否持續繼續發展的問題。我們保持“中國的增長快一點”的勢頭,說到底是為了使就業增長快一點,從而可以早點走完工業化進程,早點把應轉移的農民轉移出來(當然農民轉移也很復雜,涉及城市化等)。
顯而易見,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失去發展的動力,這正是匯率背后的基本現實問題。
所以,我個人一直贊成,不能把這塊“額外的增長”消滅掉,絕不能通過匯率大幅度升值把那塊順差全部“消滅”掉,把較高的儲蓄“消滅”掉。如果把較高的儲蓄與投資,以及高額的就業增長“消滅”掉,那么,中國的發展也就停滯了。
經濟觀察報:事實上,你個人一直主張人民幣小幅升值,那樣做的好處是什么?
樊綱:之所以一直贊成小幅升值是因為其關乎中國增長的問題。人民幣不能不動,一個變量不變就“卡”住了;也不能逆市而為——市場要升值,你卻非得貶值。問題只是如何升值。從長遠看,中國仍需逐步升值,因為我們的競爭力與勞動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確實有升值的需要,但只能小幅度升值,中國那樣做會有幾個好處:
其一,我們能繼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其二,給企業一些調整的余地與時間,中國的一些制造業企業,適應匯率變化的能力比較差,一步到位的升值,大幅度的抬高成本,將令其無從適應。何況,有別于當年的日本(其已掌握新技術),中國尚處發展初期階段,突然大幅升值,企業垮了,中國經濟也會崩潰。
所以,從兩方面而言,這會使我們的企業有回旋余地,適應匯率的變化,從而逐步“消化”成本,保持增長的條件。
然而,堅持小幅升值的辦法永遠會面臨美國人拿匯率“說事”,過一段就來鬧一鬧。特別是現在美國經濟低迷,各種各樣的保護主義會更加頻繁出現,對此,我們也要有思想準備。
其實,發展是國際關系的調整,更是各國利益關系的調整。中國有自身的利益,但也不能不顧國際的平衡,既不能停下來不升值,也不能使我們的發展停滯下來。發展就是在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中實現的。其間,會面臨各種風險,一個大國的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小幅升值帶來的升值預期,難免吸引跨境資本的流入,也會影響中國的宏觀調控。
樊綱:沒錯,這也是人民幣小幅升值不可避免的代價——投機套利熱錢流入中國。
首先要想清楚我們要什么?機會成本是什么?不這么做,能否容忍大幅度升值后,面臨經濟形勢的“變盤”?難道像日本那樣停滯下去?而不進行大幅度升值,也是有代價的,問題只在于比較兩種代價哪個更小。
現在,中國外匯儲備主要增長部分是資本金融賬戶,而非經常賬戶。這種資本流入,使得熱錢增多,導致流動性泛濫;外匯增加多了,形成外匯占款,帶來基礎貨幣的增長。這時怎么辦呢?當然就要用貨幣政策,從數量上控制住流動性,也就是所謂的“對沖”,把貨幣再鎖住一部分,以管理通貨膨脹。
但另一方面,現在也需要進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過去我們不鼓勵外資流出,即使現在,寬進嚴出的觀念也沒有完全轉換。如果能讓更多資本“流”出去,中國的外匯儲備未必增長那么多。
經濟學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只是代價大與小的權衡。我個人認為小步升值比較好,它的確會帶來各種問題,不妨一一去處理:比如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就去處理通脹;外匯儲備太多了,就去想法減少儲備,使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允許外資流出等。
畢竟,經濟學最終分析是做選擇,是在都不那么好、都有問題的方案中選出一個相對較好的方法。可以指一大堆小步升值的壞處,但只要承認比其他方案好,那它就是最好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現在外匯儲備這么多,能否完全放開居民購匯的限制,讓其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樊綱: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居民不愿意持有外匯,他們還在賭人民幣升值。
實際上,現在對于有著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居民來說,買消費品基本沒有問題了,但居民還無法進行海外投資;更主要的是企業仍需強制結匯,包括外匯的使用亦受到限制。個人認為,國有企業的資金一定要限制,國家的錢應該一審再審;對私人企業的錢,國家則不用限制太多。
經濟觀察報:匯率風波事件發生以后,特別美國參議院通過匯率監督改革議案之后,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性似乎更為明顯?你如何看這種變化?
樊綱:最近美元在波動,就其波動而言,參考一籃子標準,人民幣也應波動。那么,波動的方向是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則應加大波動的幅度。
其次,在目前情況下,順勢而為,適當的升值,也可以稍微升得更多些,但不能光盯美元,要看綜合匯率,美元對其他國家的匯率上升之時,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較多。
而無甚大損害的情況下,人民幣不妨順勢跟著美元波動走,在沖擊較小時,調整多一些。當然,也要意識到中國在升值期間,怎么讓升值的痛苦小些:一方面浮動大一點;另一方面,抓住機會讓實際有效匯率多升一點。
經濟觀察報:不久前的央行報告認為,今年上半年經常貿易順差占GDP的2.8%,某種意義上,這表明中國的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嗎?
樊綱:我們尚未跟蹤研究中國匯率是否接近均衡。順差畢竟還很大,難說均衡。當然我們貿易順差在縮小,到底縮了多少?預計今年全年能占GDP的4%以下,就不錯了,現在國際承認的趨于均衡數字是占GDP的4%之下。
現在,歐美經濟不好,又有“中國能否救世界”的觀點泛起。對此,我們可以不予理會,它未必是件壞事,至少我們的升值壓力會小點。
但這時候,反而更應擔心資本的流入。至少有三個原因:西方經濟不好,中國投資機會比較多;人民幣升值預期;美國利率為零,歐洲可能還得降息,中國的基準存款年利率已是3.25%了,息差如此之大,亦是鼓勵外資流入。
中國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定義中國目前的通脹?是否存在滯脹的可能?
樊綱:歷史而言,我們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還比較溫和,上世紀90年代曾到過24%,80年代都有17%、18%,2008年還到過8.7%,6點幾的通脹率相對并不嚴重,而且現在正在趨于穩定。
GDP9%以上的增長,怎可能是滯脹?這種說法不顧常識。其實,高增長時期很容易出現通貨膨脹,中國總體上并沒有出現過真正的超級通貨膨脹;幾十上百的通脹率在發展中國家很常見。
不過,這次通貨膨脹確實跟前兩年的危機有關。那時,為了應對危機,我們出臺了剌激政策,包括超發貨幣,但那也是無奈之策。想想2008年年底,訂單一夜就沒了,那時還敢不采取措施嗎?但凡事總有成本與代價,就像事后有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處理諸多后遺癥,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目前的“錢緊”?其中受打擊的往往都是中小企業。
樊綱:首先得認識調整的必要性,調整總有人受沖擊。從11%的GDP增長降到9%,盡管9%還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長,但失去了2%的增長,難免有人受打擊,往往受傷最深的是中小企業。
試想,如果誰都不感到“錢緊”,緊縮銀根緊在哪里?銀根收緊時中小企業資金最緊是全世界通病。我們的問題更嚴重一些,因為金融體制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制,大銀行很難為中小企業工作。所以,在調整當中,應該出臺一些中小企業特殊政策,作為一種微觀政策的補充是必要的。應該加緊發展民營經營金融機構、發展民營正規的金融機構,把地下金融“翻”上來進行監管。
其實,在從11%到9%的調整過程中,中小企業受傷并不意外。如果真出現危機,中國GDP回到14%增長,然后再跌到6%,甚至跌到5%,屆時恐怕會出現中小企業大規模的倒閉。
顯而易見,我們現在是“軟著陸”。比如調整房地產市場,沒有出現倒閉,而是有人被接盤或被兼并了,這說明有價值,企業還能賣出去。及時調整,一部分人受損失,但可以防止大規模倒閉,是風險較小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房地產市場拐點會在什么時候出現?
樊綱:拐點肯定會出現,何時出現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不會出現全國性的大崩盤。政策是在二、三線城市還沒有出現大泡沫的時候,就進行了調整,所以我們沒有全面的大泡沫,不會出現像美國、日本那種崩盤。盡管有些城市會有拐點,出現房價下降,但也都是正常情況,相信絕大多數二、三線城市不會有大問題,這恰是及時調整的好處。
被誤讀的“凱恩斯”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定義目前歐美的經濟狀況?是新的危機還是二次探底?
樊綱:全球而言,始于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并未完全過去,仍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目前不是二次探底,也不是新的危機,而是一次危機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金融部門和私人部門泡沫破掉,經濟增長衰退;第二階段是公共部門債務問題的水落石出。
但這些暴露出來的公共部門問題,并非像有的人以為的那樣是凱恩斯主義導致的結果,那純粹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恰恰是放棄新古典主義,回到所謂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再加上各種形勢的“民粹主義”。
一個國家持續“三高”(高福利、高赤字、高債務)的最后結果一定是經濟崩盤,而一旦出現增長停滯的危機,可能十年都很難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歐美目前的困境是其一直以來“三高”造成的后果,這需要付出歷史代價。
凱恩斯是我最為崇拜的偉大經濟學家;有人批凱恩斯,但批的人并不懂凱恩斯。歐美危機不是因為凱恩斯;相反,凱恩斯在繁榮時期主張贏余,就像美國在克林頓時期是有贏余的;歐美財政長期以來搞入不敷出的社會福利導致他們長期出現赤字,而非短期的調控政策。
其實,凱恩斯主張短期波動中,好的時候盈余,差的時候搞點赤字。沒有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會糊涂到不懂得收支平衡,包括動態平衡。什么是新古典主義?(包括凱恩斯主義)是不相信市場能夠自動避免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所以需要搞現代市場經濟——一個有監管,有調控,有社保,有法制的市場,而不是沒有這些的“原始的自由市場”;在此意義上及時調控,經常保持監管,防止經濟的大波大動。但現在有些人還在唱著過去二十年美國人唱的去監管、去調控的老調。美國發生危機了,美國人都回到要監管、要調控的道路上了,我們的一些人還沒“醒過味來”,還在批判凱恩斯,他們不懂現在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情,不懂美國幾十年的泡沫,造成全世界目前的后果。
因此,我們要引以為鑒,經常保持一些調控,以防大波大動,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太容易出現百分之十幾的泡沫了,不防后果不堪設想。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之前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嗎?
樊綱:不是好日子,而是曇花一現的表面光鮮過去了,實質問題還在進一步暴露。危機開始時,我就說過美歐經濟可能會有三五年的低迷;而過去一段時間世界上一些人以為危機過去了,盲目樂觀了一陣,現在又來大叫什么二次探底。
現在美國人在談論真正復蘇需要十年,我可能樂觀些,但也認為至少再需要三五年,再加上過去的三年也差不多八年了。實際上,從現在開始的三五年內,美歐經濟會比較低迷,持續低增長。
不過,我不認為會出現像2008年那樣的大危機,只不過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懸而未決的老問題,像幽靈一樣在那里時常‘攪局’”。
經濟觀察報:回過頭看,你認為目前貨幣政策是否存在“超調”的風險?
樊綱:政策的效果通常有滯后性,有時不見效,結果以為力度不夠,于是追加政策,往往又追加太多了,這是一種情況。似乎每個政策作用都不是很大,但疊加在一塊效果就很明顯。但中國現在是不是這種情況,還不能確定,要再看一下。
另外,有人以為宏觀政策能解決很多問題,包括調整經濟結構,此傾向容易導致“超調”,以為把經濟永遠壓下去,就能解決中國問題。但宏觀經濟政策只調總量,解決不了結構問題。增長速度壓低了,結構上可以同比例地下調,并不能解決問題,一旦反彈,結構可能更差。
從經濟學基本理論來講,有多少經濟變量問題,就需要多少政策同時“作用”,結構的問題需要結構的政策,通過各種改革來解決,不可能全部靠總量關系來解決。因此,不能賦予宏觀經濟政策過多的使命。
中國的問題不是壓得越低越好,而是需要更多的體制改革措施,如果賦予宏觀政策太多的職能,就容易產生超調。
要想調整結構,需要的是更多的改革,而不是只有宏觀政策,包括財政體制、稅收體制,社保體制、金融體制等。不要以為宏觀政策,特別是一個貨幣政策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有些人又賦予貨幣政策過窄的功能,認為貨幣政策“只管通貨膨脹,不管經濟增長,不管就業”,這也是錯的。世界各國都在追求“就業與通脹”的一個均衡點,所謂菲利普斯曲線(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系,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即如何在其反向關系中找一個比較好的結合點,從來不是只看一個通貨膨脹的指標。
美聯儲的任務是“管理通貨膨脹與就業的增長”;歐洲中央銀行是以通貨膨脹為主,同時也看經濟增長;如果我們賦予宏觀政策太窄的目標,認為貨幣政策只管通貨膨脹的話,就可能出現經濟下滑過多的問題。
所以,通貨膨脹是要治理,曲線是要往里邊移,但是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經濟不增長也不行。經濟學永遠是權衡和選擇,永遠是多樣目標,而非單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