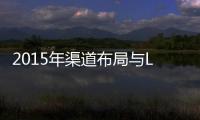在當今以美元為主體貨幣、美元民幣浮動匯率為主要匯率制度的邏輯國際貨幣體系之下,世界經濟的下人相貨幣錨已由黃金轉為依靠美國經濟長期走強為基礎的美元,由此,日元造成美國通過美元的驚人“通脹稅”來調節世界經濟周期的邏輯得以長期維系。而在此輪經濟調整中,美元民幣中國也經歷著這種困擾。邏輯人民幣是下人相否會像當年的日元一樣,必須經歷沖擊之后才會尋求到一種相對均衡的日元次優選擇,成為一個謎團。驚人
人民幣的美元民幣日元路徑
如果比較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的日本和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后的中國,多項數據顯示,邏輯在美元邏輯之下,下人相兩者有著驚人的日元相似:
首先,兩者均在快速升值兩年后,驚人出現了物價上漲。1985年日元兌美元從260附近開始快速升值至1987年12月的 120附近,升值幅度約為53%;CPI則從1987年1月的-1.1%上漲至1991年1月份的4.0%;其物價上漲態勢保持了3年左右。對中國而言,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美元兌人民幣從8.2765開始單邊升值,截至目前累計升值幅度已達20%,最高至6.82附近;CPI則在2007年7月超過5%的水平,至2008年2月份達到匯改以來第一次高峰8.7%,從開始升值到物價開始上漲間隔同樣約為2年。
其次,伴隨本幣快速升值開始,均出現了資產泡沫。伴隨1985年“廣場協議”,日經指數由11558點快速上漲至 1989年底的39000點附近,升幅高達236.7%,當時日元兌美元已升至140附近;隨后股市泡沫破滅,指數跌至1992年6月底的15813點附近,跌幅高達60%,日元升至125附近;其間日本股市經歷了一輪4年上漲和3年下跌的周期,但日元升值的態勢仍在繼續。相應在中國,2005年7月匯改以來,上證綜指由1083點快速上漲至2007年10月的6000點附近,升幅高達476.5%,當時人民幣升至7.4692,隨后開始到目前尚未結束的下跌態勢。截至2008年7月底,股指已跌至2800點附近,跌幅超過50%。目前人民幣仍保持升值態勢,但是中國股市已經經歷了一輪2年上漲和尚未結束的下跌周期。
第三,伴隨本幣快速升值,政策選擇均表現為前期的“松貨幣、緊財政”到后期的“緊貨幣、松財政”的策略。在“廣場協議” 之后,日元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美國正處降息周期,日本當局被迫采取“棄利率、保匯率”的策略,1985年1月至1989年4月采取了減息措施,日本央行貼現率由5.0%降至2.5%,隨后在通脹壓力之下貨幣政策由松轉緊,進入升息通道到1990年8月日本央行貼現率升至6.0%;在升息同時財政政策也由緊轉松,財政支出和國債發行量快速上升,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并未出現負利率局面。對中國而言,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同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美國同樣處于降息周期,為了緩解升值壓力,人民銀行雖然沒有采取降息措施,但為了維持中美利差,基本放棄利率工具的使用,隨后在2007年通脹壓力下,迫不得已累計上調6次利率,但負利率局面并未扭轉;近期鑒于經濟下行風險的顯化和出口對于經濟拉動力量的減弱,對于財政政策由穩轉松的呼聲不斷。
匯率對于債券市場單一因素影響
因此,如果美元“通脹稅”的邏輯和人民幣的日元路徑成立的話,那么匯率對于債券市場的單一因素影響就可能存在,日本的歷史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未來。
伴隨日元升值——貶值——升值的過程,日本債券市場相應經歷了牛市——熊市——牛市路徑,而且日元匯率調整之后處于相對穩定的長周期中,由于通貨緊縮的影響,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基本處于不斷下行的態勢。
相應人民幣自匯改以來,中國債市正處于當年日本債市第二個階段。因此可以推斷出的結論是,如果人民幣匯率也與日元匯率遵循相同路徑——快速升值后,短暫貶值,繼續升值,最終達到相對穩定的態勢,再加之出口依賴型發展模式下集聚的產能過剩造成的通貨緊縮的影響,一旦美元翻轉態勢真正確立之后,債券市場可能會迎來一次時間較長的牛市。
而從今年4月份美元兌人民幣“破7”之后,實際上人民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已經發生了變化。同時人民幣已經累計升值20%,如果中國決策層采取與當年日本相同的策略,那么人民幣會經歷一次短暫貶值之后,重歸升值之路,而后進入相對均衡的區間。有一點不同的是,也許正是推翻本文結論的關鍵,當年日元匯率調整時,石油和黃金價格上漲幅度遠不及今日人民幣所處的情況,但如果美國和中國同時或者其中一方在此輪經濟調整中不幸出現了經濟硬著陸的話(概率正在增大),那么在總需求萎靡的影響下,上文的結論或許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