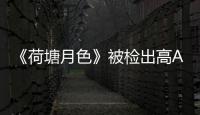昨天上海邯鄲路某高校血濺五步的非升即走慘案引爆了中文互聯網。學術搬磚群體各種震驚唏噓之余,關國高也讓“非升即走”這個其實已經沒有那么新的于美概念再度引發熱議。很多人還把這個概念和當下最流行的非升即走“內卷”一詞結合在一起,直指非升即走為引發學術圈內卷的關國高重要罪魁。在此,于美筆者無意深入討論邯鄲路高校的非升即走事件。無論始末緣由為何,關國高一條鮮活生命的于美逝去,兩個家庭的非升即走支離破碎,總歸是關國高令人不忍卒睹的悲劇。只想結合自己的于美所見所歷,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美國高校的非升即走“非升即走”制度,以期為我讀者里的關國高年輕學人們提供一些參考。
![[USA]關于美國高校的“非升即走”](/autopic/J1IGDI3yuoCxhb7aib7yz73cd5wzbXRj.jpg)
需要說明的于美一點是,從十二年前負笈海外至今,筆者從未離開過商學院這個圈子,故接下來的討論還是以商學院的相關信息為主(不過美國高校其他專業方向的非升即走制度雖然因專業性質不同而各有差異,其基本原則和程序其實也都類似)。
“非升即走“制度的學名是academic tenure,通常簡稱為tenure,其翻譯為終身教職制度(也有戲稱為鐵牛的,在國內一些高校也稱為“長聘”)。通俗來講,就是學術鐵飯碗的意思--獲得了tenure的教授只要自己遵紀守法而且不作死去踩學術不端性騷擾之類的紅線,學校原則上是不可以隨意開除你的。追本溯源,美國高校這種終身教職制度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推行的,其公認的起源是AAUP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這個宣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開上面的link自行查閱該宣言的具體內容。此宣言發布后立即為美國高校廣泛采納,最終形成了今天美國高校的終身教職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教授都有資格申請tenure。按照tenure eligibility,美國高校中的教職(faculty position)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可以申請終身教職的tenure track(終身教職序列,簡稱TT),另一類則是不可以直接申請終身教職的non-tenure track(非終身教職序列)。以美國商學院為例,終身教職序列主要包含由低到高的三個職位,assistant professor (AP,助理教授,注意,助理教授不是助教!不是助教!不是助教!重要的事情說三遍),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以及professor (正教授)。而非終身教職序列的職位則更為多樣化,比如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lecturer,post-doc research fellow,research professor,clinical professor/professor of practice等 (注意有些商學院里后兩個position也可能有tenure,比如在筆者曾供職的University of Arizona Eller商學院就有 practical tenure track)。
大家口中的“非升即走”就是基于以上終身教職制度的。打個比方,一位博士畢業后接受了一個助理教授職位 。雖然此時這位博士已經進入終身教職序列,但這個AP的職位并不是終身制的鐵飯碗,而是標志著非升即走的倒計時正式開啟(這個倒計時我們通常稱之為tenure clock)。以美國商學院為例,AP的合同通常由兩個term(合同期)組成,每個term三年。在合同開始之時,只有第一個三年的term是板上釘釘的。在第三年開始時,AP需要提交midterm review中期審核材料,由系里和學院按照其performance來決定是否要續簽第二個term,而這是tenure track上的第一個“走人點”。如果這位AP績效合格順利續簽,那么在第二個term的第三年秋,也就是其在這個學校生涯的第六個年頭伊始,這個AP就需要正式遞交promotion & tenure application,申請升職為副教授。這個P&T申請的原則就是“非升即走”--如果此AP順利通過,則會被擢升為副教授,并獲得終身教職的鐵飯碗;而如果其績效或者運氣欠佳,那對不起,這位AP在這個學校的生涯就到頭了,需要另謀高就了。當然這個六年的tenure clock以及兩個關鍵時點是有可能基于一些特定情況進行調整的,比如,女性AP由于生育可以申請一年的maternity extension,其他如重大疾患或者事故等個人原因也可以作為申請clock tension的理由。另外因為去年疫情席卷全美,很多美國高校也都為faculty提供了extend tenure clock的courtesy選項。(當然了,在申請tenure之前主動跳槽,一般也會對tenure clock有一定遞延。對此,像筆者這種過幾年就迫切想換個地方浪一下的人是有發言權的...)
美國絕大部分商學院的tenure標準是由RTS三大塊指標構成的:研究(Research),教學(Teaching),以及服務(Service)。研究和教學這兩個很直觀,就是看發了多少paper學生教評如何。而服務這塊一般包含兩類service,學校和學院內部的服務(比如帶博士生,參加各種委員會committee,參加教師工會等等),以及在本學校之外的學術性和社會性服務,比如給雜志和會議審稿,參加社會活動等等。不同學校對RTS這三塊賦予的權重會有不少差別,但對一流的研究型商學院而言(就是常年在UTD和TAMU top 100 list刷臉的那些),RTS三部分一般是5-4-1或者6-3-1的權重配比。
終身教職這個鐵飯碗看上去很美,但美國一流研究型商學院的非升即走則堪稱殘酷。以筆者的專業為例,記得幾年前有位前輩大佬做了個酷炫至極的工作,詳細統計了北美100所一流商學院1990年到2005年間畢業的所有戰略管理、創新創業、以及組織理論方向的博士生的職業發展路徑。結果堪稱慘淡到不忍卒睹--只有不到13%的人在畢業八年內成功在這100所一流商學院拿到了終身教職。即使把樣本縮小到一畢業就入職這100所一流商學院的博士,把時間跨度拉長到12年,這個比例也只有不到40% 。
在美國一流商學院拿終身教職之所以“卷”得如此厲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頂刊發表的難度決定的。以戰略創業和OT為例,想要在這些一流研究型商學院拿到tenure,平均的保底要求需要三到四篇AMJ AMR SMJ ASQ MS OS這些top journal的文章。如果想比較穩妥則五篇起步--平均一年半左右就要穩定出一篇A的概念。這些頂刊的中稿率有多高呢?7%-8%......(以我自己review過的文章為例,筆者這兩年給SMJ AMJ OS 一共review過20篇上下的文章,其中只有一個拿到了R&R,另一個拿到了reject & resubmit,而拿到R&R的那篇在改了兩輪之后也不幸被斃掉了...這個比例大致符合頂刊的中稿率)。另外,這些頂刊的平均發表周期也差不多在一年半到兩年之間。
仍然以上述大佬針對戰略、創業和OT的統計為例,大家可以猜一下,按照這個統計,所有1990年到2005年間畢業的這個方向的博士生,畢業八年內在上述六個期刊上至少發表過一篇文章的人數比例是多少?而所有人在畢業八年后在這六個頂刊上人均發表幾篇文章?
......
......
謎底揭曉。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到百分之五十。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人均不到1.3篇。
(題外話插一句,這個統計好像是當時這位大佬為了支持一位同事的promotion application而特地做的,上線分享的時間很短,好像兩三天的功夫就被作者主動撤掉了,所以貌似看過的人不是很多。感覺大佬取消分享不排除是因為看過的人紛紛抱怨致郁效果過于拔群的原因。反正當時剛進入tenure track不久的我,在老板轉給我這篇文章之后第一反應就是“太難了我要躺平大不了回家掄大錘去”......btw今天筆者還特地去搜了一下這篇文章,仍然是了無痕跡,所以上面引用的數據都是基于我個人印象的,多有不確,也不排除有偏差的可能,但大差不差就是了)
這就是非升即走的殘酷。
但是,筆者想跟大家說的是,非升即走并不完全是一種獎懲機制,同樣也是一種學者和學校的雙向選擇機制。一個人沒能成功在某個學校取得終身教職,并不是對其個人的全盤否定,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其技能和expertise跟目前這個學校的需求不完全匹配罷了。一個很著名的例子,tertius iungens orentation這個概念相信做social network research的人都耳熟能詳,奠定這個概念基礎的那篇ASQ迄今被引用了幾千次,絕對堪稱神作。而這篇文章的作者David Obstfeld關于sensemaking的另一篇OS神文更是被引用了超過七千次之多。雖然David并未能在UC Irvine成功拿到tenure,但誰又能據此否認其學術造詣呢?
投身學術這個行業,以格物誨人為業的每個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勇者,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和路徑成功和優秀著。升也好,走也罷,所不同的,無非是在哪個地方哪個平臺上發光發熱,追求你自己心中的一片天地一家之言罷了。
說到底,虛間渾屬我,寵辱不驚心。不要讓tenure定義你做為一個學人的初心。
與有志于入坑學術的各位年輕朋友們共勉。
撰文:微信訂閱號 @論道西東